|
想必前世我是在这里住过的,不然我不会踏着浪花急促促地飞奔而来。
环岛的山路上,光影依旧魅惑地跳跃着,山路上方潮湿的沟涧处,卷丹百合也依旧浓烈地开着,且与岛上浓密的植被浑然交汇在一起,相映相称、相依相靠,就仿佛前世的某一天,我踩着那些光影拾阶而上看到的那样。路旁的合欢树早已结出了一嘟噜一嘟噜的荚果;成片的爬山虎更是诗意地爬过一段段石墙,或是一座座独立的山体;青松遍地,数不清的金银花、石竹、山草莓、棒棒枣夹杂其间;我甚至还看见面前凸出的绝壁上那一簇开得无比空灵绝妙的地枣,看见几串挂在枝头似是有些意犹未尽的槐花。一切都是惯常的姿态。 前世,我一定来过这里或是在这里住过!我在心里说。
不然,坐在宽敞明亮的院夼村会议室里,听了老书记为我们讲述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拥军历史,心里不会有一阵又一阵的暗流涌动,就像惊涛骇浪的天气里,疯狂的浪花扑打礁石所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声响“啪——啪啪——” 相信所有土生土长的荣成人对于这样的讲述都会感同身受,伴着老书记动情的讲述,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:寒风肆虐的冬日,海上风大浪高,旧时的小渔船摇摇晃晃地行驶其间。突然一个巨浪打来,小船便一个趔趄,冰冷的海水打湿了船上渔民本就单薄的衣衫,过度的疲劳与寒冷一点点耗尽渔民最后的气力,是苏山岛灯塔上明亮的灯光照亮了渔民前行的路;当拼尽最后一丝气力把船停靠在码头时,是那些驻岛的战士毫不犹豫地拿出他们的军大衣给冻得浑身发抖、牙帮打颤的渔民穿上;是驻岛的官兵烫了热乎乎的老酒、烧了滚烫的饭菜为他们端上桌来。热炕头上的那一幕,一定深深地刻在每一个风里来浪里去的渔民心中。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院夼村村民也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切,从最初的手摇大橹到机帆船,再到现在的大马力渔船,自发地担当起为驻岛官兵免费运送物资和接送出岛的任务,并为守岛官兵家属提供免费的食宿,几十年如一日,从未间断,其间历经的故事说也说不完…… 也曾有人问过老书记:“你们坚持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?” 老书记的回答只有简单的几句话:“没有为什么,只是觉得军民就是一家人,就像人与空气一样,虽然看不见,但一刻也离不开;又像是一对亲兄弟,一方有难,另一方当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。” 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回答更令人打心里钦佩、折服!我知道,我感动了!在那一刻,我彻底地感动了。
在短短一个小时的讲述中,我的心灵深处早已铺展出一幅博大的画面。包括院夼村、包括苏山岛、包括所有我未曾经历的海上春秋,那些画面是如此清晰,并在这个雨声淅沥的正午一点一点蔓延至我的眼前,浸透进我的生命。就像岛子上四处可见的那些掩映在绿荫深处的“毅”“守”“磐”“坚持”等等。每一个字都透漏出守岛官兵的坚毅与忍耐。那些漫漫长夜、那些雪打风吹、雨啸雷吼的日子是可以想像的,如此,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守岛官兵尽一份微薄之力呢? 事实上,院夼村做到了,半个多世纪从未停过的拥军航线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。 院夼村与苏山岛——世世隔不断的鱼水情。
|

 手机版
手机版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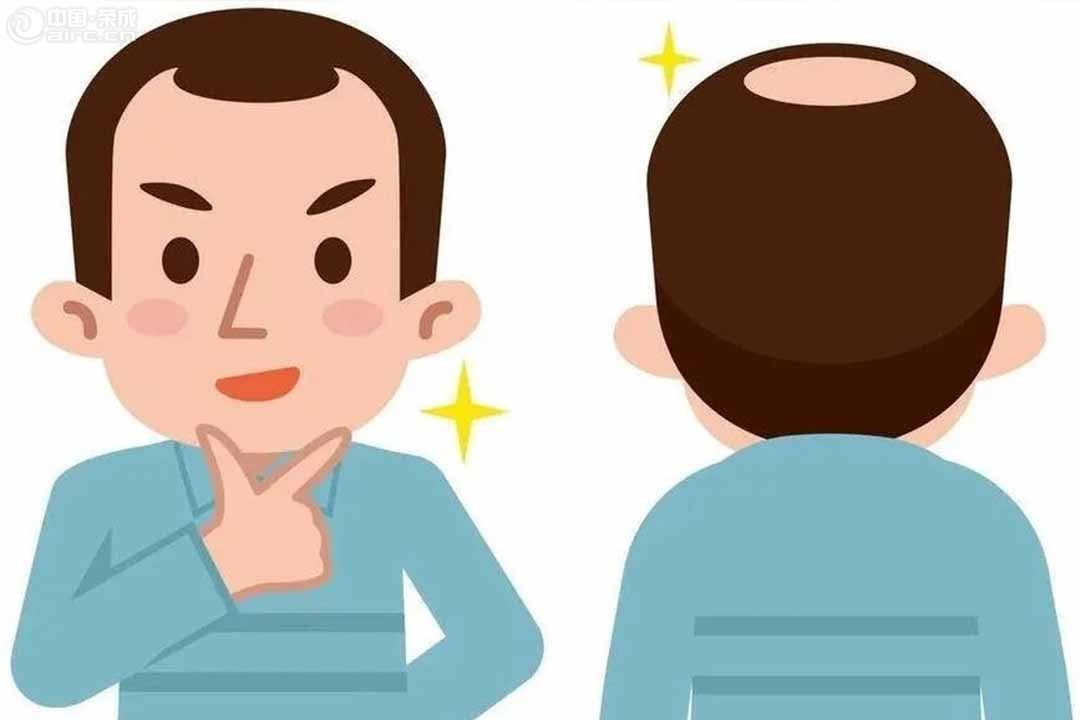



 鲁公网安备 37108202000325号
鲁公网安备 37108202000325号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