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又到盛夏,不知不觉地想到了河南村的十亩荷塘。
我觉得,尽管城市的扩张,早就将河南村划入了城市的建制,但于四面的巨变中,这时依然保持着幽静,保持着都市里的村庄个性,就像我对十亩荷塘的定位一样,虽然他属于园林式的产物,但于主人心胸的豁达之下,它,俨然成为大众渲泻情感、放飞心情的最佳场所。一池荷香,如清醇的乡土芬芳,醉了东西南北人!
六月的荷花最美。它,妖妖娆娆、光彩夺目地恣意绽放,引无数文人骚客为之泼墨,描绘它的绝世倾城。 其实,自媒体时代下技术革新的推动,追逐荷塘美色的已不再限于文人骚客,更多的人凭借着移动终端、借助着微平台步入了发现美、欣赏美、传播美的的链条中。但不管是谁,只要走近了荷塘,都会觉得自己已远离喧嚣,情感在沉淀。
于乡村的荷韵中,十亩荷塘属于园林式小家碧玉式的家庭景观。 一般而言,乡间的荷塘都是敞开式,其夏荣秋枯都任期自然转换,极少有人关注。于十亩荷塘这儿,却是经过人工的雕琢,池塘的周围杂以湖石,湖边的树木也可能经过精心的挑选与设计,何处植柳、何处栽竹,何处种草,一定是经过精心的构思。倘若如此,那些仿古式的建筑,一定是几番刻意的布局。精致,到过这儿的人们,谁都无法否认这点。
现在的十亩荷塘,已成为闹市区,城铁荣成站的落户,以及周边现代建筑的崛起,让这里暂时以村居之。当年的僻静已为闹中取静。来此赏荷,交通便捷,自然就来者云集,门庭若市了。

三分荷塘,七分心。不管是谁,移步荷塘前都只为静静地欣赏一幅绝美的图画: 碧绿的荷叶,如伞。若中在露,常常会有几滴露珠在叶面上闪着灵动的光。碧绿的莲叶布满湖面,接天蔽水,无穷无际;碧叶之上,娇艳的荷花像亭亭玉立的仙女,灿烂地绽放着,与太阳交相辉映,红妆妖艳别有一种风韵。
莲蓬像个规整的漏斗,有淡黄的缨在斗的下方周围垂着。荷叶的缝隙间,又有新长出的叶,如同一柄柄刺向天穹的剑。只是在剑尖上,却没有蜻蜓,但这丝毫不影响一池荷韵。 “毕竟西湖六月中,风光不与四时同。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 宋朝诗人杨万里的这首诗,写的应该正是此时的荷花。
又大又圆的荷叶,让人首先会想到一个叫“碧玉”的词。荷塘里,荷叶挨挨挤挤、层层叠叠,像无数个小雨伞。那天雨后,有风吹过塘面,霎时间,千万支荷伞随风舞动,荷叶翻转形成了一幅壮观的绿浪,让人为之振奋,引来赏荷人的阵阵喝彩。与以往的幽静相比,那天的荷舞更动人心弦。
眼前的荷叶,感染人们的,是它的旺盛的生命力,它的勃勃生机,还有它的无私的奉献精神。它的生长,只为大地增添绿色,只为荷花衬托绿意,只为泥土下的藕进行光合作用。 微风拂来,荷叶舞动。赏荷人都如荷一般漂浮在这绿波涌动的水面之上,随心所欲,翩然舞蹈……如果心态再放低一些,俨然就是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。 赏荷,满眼滴翠。 观花,清香一片。
走近荷塘,我常为乡间荷塘之顽强而感佩。乡间的荷塘,大家都经历过波折和浩劫,有的消失于改造自然之中,有的却几经磨难,初心亘古不变,最终成为人们的情感寄托之地。
这些年,我走过乡间的许多荷塘,我发现几乎每一个荷塘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 在一个小一型水库的一个村子,当年因为取水修坝于1950年代末形成了一个几百平方米的水湾,人们沿湾生活,取水浇地,仅此而已。1980年代,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,人们决定在湾内种藕养鱼,不料遭遇一场几十年未遇的旱灾,当年的滨城,在八家大型企业因缺水停产,二十万人、三万头牲畜饮水困难。旱灾让河塘干涸,人们种藕的想法化为泡影,埋下的藕根任为太阳暴晒、鸡刨鸭踩。此时,有一位老妪,迈着小脚,提着水桶,一次次地为残藕浇水覆土,希望奇迹出现。
后来,一场暴雨让水湾泛起水波。过了一段时间,人们发现水面上窜起了几丛荷叶,后来还绽放出荷花。又一个冬春过去,这里已经是荷叶田田,一池荷香,成为人们赏荷最佳目的地。
|

 手机版
手机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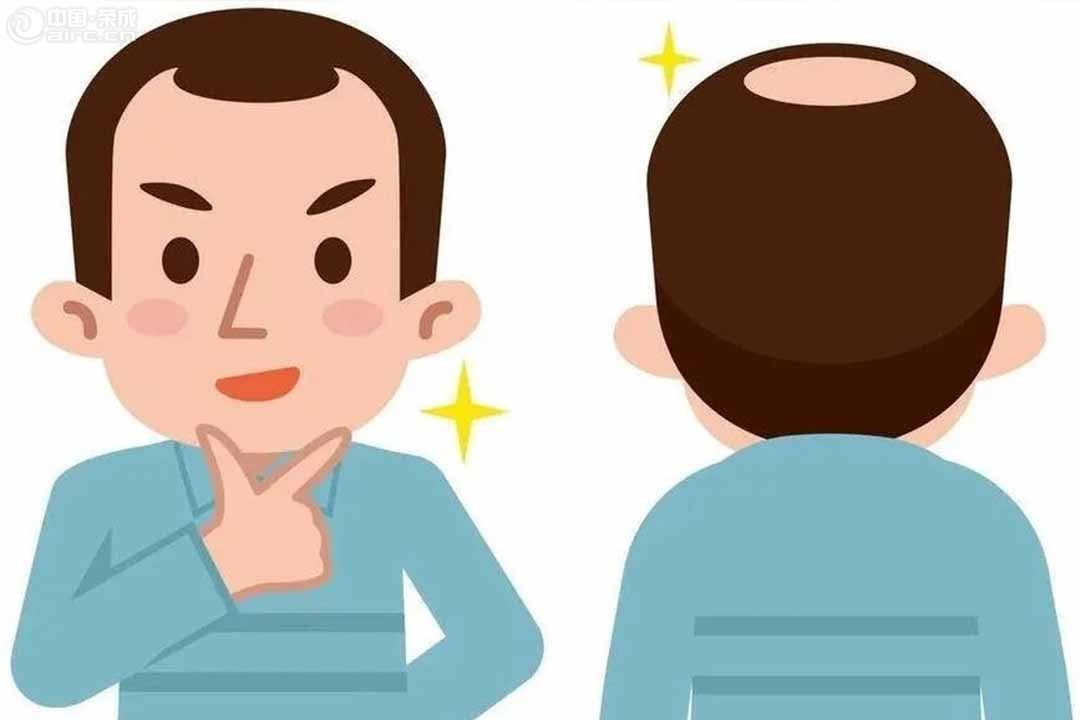



 鲁公网安备 37108202000325号
鲁公网安备 37108202000325号





